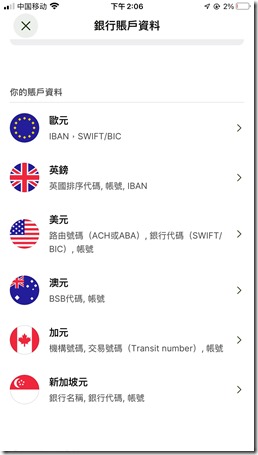有這麼一個人,你叫不出他的名字,甚至沒見過他的樣子,但你從小到大看過的電影片名,大多都出自他手。
那些你能想到的大片,你能回憶起的片斷,王晶、杜琪峰、王家衛……當影院的燈光慢慢暗下來,你看到銀幕亮起,他寫的片名一個字一個字顯現出來。之後,你將為兩小時的故事或哭或笑,青春年少,五年十年,一晃就過去了。
星爺早先的《逃學威龍》,浪子回頭的《食神》,多年後淚目過很多人的《大話西遊》,還有,《美人魚》……
這個人,叫馮兆華。筆墨不止霸了香港電影的半壁江山,甚至佔了香港街邊那些招牌的半壁江山。
馮兆華有個筆名——華戈,戈卻不是哥。1979年從內地移居香港,在這個城市有過和所有年輕人一樣的茫然無措。
他說自己不會稜稜角角,幾十年都沒跟別人吵過架,朋友說他軟弱,不如名字改硬氣些——「用那個戈啊,武器那個戈」,「也好哦」,他想,於是順理成章用到現在。
或許真的和朋友講的那樣,華戈性格軟,連那場成為他人生轉折的書法比賽,還是別人慫恿着他去的。
拿了獎之後,開始有人找他寫字,一次能賺100塊,平時打工可要賺三天。
原來寫字也能養活自己啊,而寫字又剛好是自己一直以來最大的愛好。
家裡的長輩們喜歡書法,哥哥姐姐們也在學,小時候他總用他們用剩下的毛筆在地上寫字。就連在打工的時候,也要抽空練字。
他覺得,自己是用最不好的筆,寫最好的字。
31歲,華戈決定入了寫字這個行當。
活是自己找來的,星期一走黃大仙、樂富,星期二走牛頭角上下邨,星期三觀塘,星期四深水埗。
星期天走遍油麻地和旺角,見哪家店鋪的招牌舊了,就主動幫忙翻新。
寫的時候不知道收多少錢,都是讓人家看心情隨便給。「收入好,有大肉飯吃;無生意,只好叉燒包填肚。」
香港就好在,它能給任何人成為藝術家的機會。
那時候華戈有位最佳戰友——一個油跡斑斑,印着卡通公仔的布袋子。是從垃圾桶里撿的,裝着油漆和刷子陪華戈走過許多街道巷口。
1983年,華戈在缽蘭街花2800塊盤下一個檔口,專門寫字。附近有唱片店、理髮店,也有印卡片、配鑰匙、賣牛仔褲的,街頭燒飯隨處可見。
來來往往圍着看華戈寫字的人很多,警察有時候路過嫌擋道,會讓華戈停筆。等人都散完,重新開始寫,這時候人群又會聚過來。
人多吵了,華戈也不介意:寫字要是沒人看沒人評論,那還有什麼意思。
餐廳老闆來找他寫菜牌,結果總被人偷了去——華戈的字,靚。
香港街頭因為招牌的存在而迷人。
樓房之間伸展開來的各種白底招牌,紅色為主的油漆字總是很醒目。這是華戈當時接的最多的「白手招牌」,美心啦,富臨啦,黃銘記啦,英華書院啦。
酒樓的字要敦厚寬容,書院的要端莊穩重,武館社團,主要看氣勢。
華戈還爬上過28樓高的大廈寫字,不打草稿,腰上系根繩子,腳勾住竹棚,慢慢往後傾斜身子,因為越往外越能看得清楚,看清看全了,才能把字寫好。
左手提油漆,右手揮筆,速度就跟表演特技似的。
「危險嗎?」
「危險也認命。做了這行,就要做到最好。」
那時檔口邊上有家賓館,總有明星藝員來住。
「這些都是你寫的?」
「是啊。」
「再寫幾個看看。」
問話的是當時香港電影的大哥洪金寶,一個介紹一個,華戈就這樣入了行,也成了電影背後不可缺的人。
一開始只在片場寫些道具字,1989年,華戈第一次給電影寫片名,劉德華和鍾楚紅主演的《愛人同志》。
劉偉強找他寫,古惑仔從第一部開始拍到最後一部,海報上的四字成語,都是華戈寫的。
黑社會的題材,杜琪峰也找他寫
80、90後絕對都看過的賭錢系列,也是王晶找他寫的。
華戈給電影寫字,都要先看過電影。
比如說《魔警》,並不是說警察是魔鬼,而是這個警察又多重性格,主角覺得自己是警察,又是執行者,又是判官。
所以必須在魔警這兩個字里,體現出這些點,可又不能把字寫得面目猙獰。
比如《倩女幽魂》,小倩和寧采臣的相遇跟離別,都是天註定。可人和鬼能相愛嗎?不能的
所以,就要寫出幽幽怨怨、斷斷續續,藕斷絲連的感覺。
人人都說王家衛難搞,《春光再現》拍了那麼久,最後把關姐姐演的女主角戲份全剪了;梁朝偉拍《阿飛正傳》最後那幾個鏡頭,被墨鏡王折磨到懷疑人生覺得自己不會演戲。
可輪到華戈給《一代宗師》寫字,卻是一遍過。
甚至王家衛還把電影里,所有招牌都交給華戈來寫。
從入行到現在,華戈寫過不下60部電影的片名。
受歡迎,皆因肯變。
被問到哪部讓他印象最深,他脫口而出是《跛豪》:「內地朋友看到了這兩個字,就知道是我寫的。才知道我過來香港了。」
——這個時候突然理解了,華戈所說的,人寫字時透的那種靈氣,跟看電影看小說,做閱讀理解都是一樣的。
很多人都會問華戈同樣一個問題:「會不會擔心書法會被電腦取代?」
這時候華戈總是笑笑,在他看來,電腦字體,李嘉誠用,隔壁擦鞋檔也用,沒有靈氣的東西,誰都可以接過去。
但他自己的書法,卻很難被別人偷去。別人學的,不是內里,只是臨摹到表皮罷了。
工作室里沒有電腦,最先進的電器,大概是電視機了。
幾年前年華戈開班教人寫字,搬到了大些的工作室,一個禮拜教六天,但從前缽蘭街那個檔口,他還留着。
寫字之外的事,華戈提得不多。經常講到的是學生和托他寫字的客人。
一到過年,華戈都會給老客人寫字。「多年來,他們不離不棄,移了民也來見我,我很享受。」
有人說華戈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,烈日當空滿身油跡去找那些招牌生意,膽子大到徒手爬上二十多層的高樓。
像極了上一代「獅子山下」的故事。
路邊的招牌或許不再像許多年前一樣精彩,華戈手中那支筆,依舊如常。夜裡的香港會在電影閃爍的霓虹里永存,而白日香港,會在華戈的筆墨里保留。
浩瀚煙波里懷念往年,外貌早改變,處境都變,而情懷未變。
本文已獲得公眾號Hey且慢授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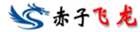 赤子飛龍_愛生活_愛網賺
赤子飛龍_愛生活_愛網賺